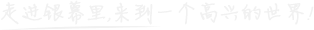影院建设

小说《白鹿原》所带来的影响力和争议性给电影《白鹿原》提供了先天的机遇,那是一次绝佳的商业与艺术共享的机遇。在中国电影当前的商业与艺术不可兼得的境遇下,这种机遇显得弥足珍贵。筹备9年,拍摄3年终于得以在银幕上呈现的电影《白鹿原》却差强人意,被世人诟病为《田小娥传》,本来的史诗巨著,被偷梁换柱成了“家庭琐事”,这是2012年最大的电影遗憾。号称“最难改编成电影”的小说《白鹿原》,树立起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标杆,其间所涉及的人与土地,情欲,战争,价值观,思想文化传统,都给一部伟大的电影留出了足够的改编空间。正是因为它太宏大,太复杂,太深邃,太深刻,所以人人都觉得“最难”,换一种角度想,其实并不是“难改编”,而是“没人改编”。从当前中国电影创作的环境看,这样的题材的确无法完全融入进去,硬往里塞,结果想当然。王全安这么做了,这个曾经靠《图雅的婚事》问鼎金熊奖的导演,给人证明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中国电影的虚伪性,必然是其衰落的根源。
电影《白鹿原》原先由写出过《霸王别姬》、《活着》的著名编剧芦苇执笔,而后他放弃了署名权,在众说纷纭中有一种说法是王全安很自负的自己进行了重新改编,借用了芦苇剧本的结构和部分内容,拍出了这个版本的《白鹿原》。接近于5个小时的时长,很多专家学者看罢均评价为“史诗级”。而从柏林参赛的版本和最终上映的版本看,即便是不懂电影的普通观众也大多数评价“坑爹”。最为诟病的就是剧情支离破碎,看罢小说的观众更是评价说,不知道导演要讲什么,根本不像《白鹿原》(小说)。也许是因为审查和上映等原因,导演删减掉了许多的情节的结果,但是就电影而言,它是双重属性的,艺术是其精神价值,而商业则是其存在的基础,一部电影的好坏,最终还是以最后的呈现方式来做评判对象的,电影《白鹿原》的差强人意,本不该再找其他的理由。电影《白鹿原》的失败,最大的问题按照芦苇的说法,就是败在了剧本上,败在了叙事上。从电影《白鹿原》的主演之一张丰毅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好导演是会做减法的导演,如果剪出来是五六个小时就不算成功。像以前很多导演都有这样的功夫,比如凌子风、水华、谢晋、谢铁骊,他们已经在分镜头剧本上把片子的长度决定下来了。而现在的导演都是大量地拍,而最后剪不下来,一剪就会出现把很多重要的东西删掉了,这就是导演的问题,也并不是王全安一个人会这样。”这段话就直白的说明了这部电影在创作之初就已经走错了路。笔者有幸看到了芦苇先生写的《白鹿原》剧本第六稿,其时长大约与现在上映版时长均等,但是叙事完整,人物线索清晰,矛盾冲突激烈,主题意味浓重。对比电影来看,则完全断掉了叙事上的线索。那么为什么《白鹿原》有了一流的投资,一流的演员,一流的技术,依然得不到一流的电影呢?最主要的问题出在了剧本身上,延伸的说,是导演王全安身上,再延伸的说,是整个中国电影创作环境的使然,是价值观的一种歪曲。
一、影像与叙事分离为哪般
电影《白鹿原》信誓旦旦的去了柏林,结果得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摄影艺术奖”。这方面看来,电影中的影像风格还是得到了认可的。从上映版本中看,纪实性的影像风格依然如痴如醉的将整个渭河平原的麦田、夕阳、冰河、村落表现的淋漓尽致。王全安电影的影像风格摆脱不了这样的冷静的客观的态度,从他的《图雅的婚事》、《团圆》、《月蚀》等电影中都可以很清晰的判断出这种影响风格的独特魅力。纪实性的影像是一种“看待”的态度,观众可以通过这种冷静的,几乎不加任何“态度”的视角看待电影中的人,电影中的事,电影中的场景,乃至电影中的精神透射,这本身就是导演的“态度”,他要观众直观的去看待,然后去思索。纪实性的镜像在电影《白鹿原》中也被大量的运用了,除了鹿兆鹏、黑娃和白孝文烧麦、黑娃砸祠堂和黑娃打伤白嘉轩等少数几场戏具有了戏剧性的影像冲击力之外,其他一概使用了冷静视角,镜头迟缓推移,都被大量的纪实性“语言”包围。就像是一个学生的摄影作业一样,毫无逻辑可言。
电影是一个综合体,影像,声音的元素某种程度上只是导演创作的手段而已,它们本身都要在影片的主题和精神价值的指导下与叙事和人物融为一体,叙事的中心也是突出和展现影片的主题和精神内核。电影《现代启示录》的影像风格正是建立在与人物塑造和叙事的基础上的,光线、音乐、镜头的运动都带有了导演的主观意图。而这种意图本身就是建立在影片的主题和精神内核上的。反观《白鹿原》的主题是什么?小说中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是人与土地命运的抗争,是两代人价值观的冲突。而电影中呢?毫无任何痕迹在表现这部电影有一个清晰的主题倾诉。人与土地的抗争,在电影中,几乎没有提及,而两代人的价值观冲突,也紧紧用了白鹿两家父子之间表皮上的讲述而已,压根没有深入到骨子里面去。倒是田小娥的悲苦命运被表现的很好。田小娥的叙事线会是像“图雅”那样沉默寡言而又暗流涌动吗?不是!田小娥本身就是一个不定性的因素,她是整部电影情感线波动的一个主推动力,是充满了戏剧冲突的。那么于哪边讲,影片的纪实性影像都无法深刻的表现出这部影片叙事本身的价值。更何况,那些出现十数次的构图精美的,色泽饱满的白鹿原大远景,没有任何的“故事”痕迹,最终沦为了给影片“分段”的工具。
当然,有人质疑说,为什么《白鹿原》不能用纪实性的影像风格?当然,看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这本来就是一本真正的戏剧张力十足的故事,是情节剧,是悲剧,是正剧。拿着老村长的酒瓶子装茅台的酒,你觉得还会卖钱吗?
二、模糊的戏的指向性
电影《白鹿原》最让人觉得头晕的就是每一场戏到底做什么用是模糊不清的。一百多场戏中,能有起到前因后果作用,或者起到了线索串联作用的戏不足3成。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看完了感觉故事像是一段一段的原因所在。有人辩解说,5个小时版本里肯定会讲清楚。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只是现在的版本,登上大荧幕,你不能拿任何的借口来解释。按照剧作法的角度说,尤其是戏剧剧作法,要“从高潮看统一”。一部电影的重点自然是在“高潮”上,但是高潮之前的铺垫是重中之重。没有了铺垫,自然不会有推动力,没有了推动力,自然高潮也不会有。电影《白鹿原》的高潮戏在哪里,也一时半伙判断不出,按照时间算,应该是“田小娥之死”。那么看来,电影还是《田小娥传》,那么为什么电影开始了25分钟,“开端”段落已经结束了,才让田小娥这个全剧高潮中的重要人物出场呢?这本身就违背了剧作创作的基本规律。前25分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皇粮被抢、鹿子霖当相约说明了改朝换代;鹿三闹事说明了世事不济;鹿兆鹏逃婚说明了新思想的萌生。但是这些情节只是一个过程,是整个故事的背景,这些事情与后面的“线索”上的联系微乎其微,大概也只有鹿兆鹏逃婚有些许关联罢了。
电影《白鹿原》中有许多戏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前因后果”。比如黑娃烧麦戏之后,一个老人站在白鹿原上木讷的说:“白鹿原是个好地方,你把我杀了,你也拿不走”,这是在表达什么?模糊不清。此外,黑娃认完干爹之后,两个小孩在麦地里翻滚,同样是指向不明。连最早发不出的《将领》一段,也仅仅沦落了展现民俗的段落,与全片叙事没有分毫联系。
一部电影,其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要为其他部分负责。串联起这个整体的东西就是影片的主题。电影《白鹿原》的主题混乱性,导致了它的剧作上是松散闲置的。从芦苇写的剧本中,则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的表达重心,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人与土地,两代之间的价值取向。虽然芦苇的文学剧本中,也是使用了“年代大事记”的方式,用年份划分出了段落,但是整个剧本中以白孝文、黑娃和鹿兆鹏,与白嘉轩、鹿子霖和鹿三的对比梳理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变化路线,期间穿插了田小娥这个悲剧角色,辅以那个时代的天灾人祸,构造出了一条比较清晰且连贯的戏剧冲突线。两代人跨越十数年的恩怨情仇,在每一个情节点中都有着较为清晰的表现。而电影《白鹿原》仅仅成了一个中学历史教科书般的“大事记”。
三、阉割掉了的仪式感
小说《白鹿原》的导演人选从四代的吴天明导演,再到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都没有人接受,最后被新生代的王全安拍成了。当然,结果先不去评论,我们仅仅就小说中所反映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核来做一点评述。
人与土地的抗争,是陈凯歌第一部作品《黄土地》的主题,陈凯歌的电影善于文化反思和发掘出正剧中所应该能有的精神价值来,《霸王别姬》就是典范,何况小说《白鹿原》中为人称赞的“求雨”一段与《黄土地》中的“求雨”自然有仪式上的先天的媒介性,所以芦苇最早是想让陈凯歌来拍,但是陈凯歌没有接受。而后的人选是张艺谋,张艺谋拍出了《活着》这样的正剧,那么芦苇与之合作,也许也会有一个好的作品出现,却也没有成功。如果具有偏见的说,《白鹿原》的宏大叙事、深厚主题是很适合五代导演的电影风格的,因为他们的电影中有仪式、有隐喻、有寓言、有民俗,而小说《白鹿原》的文化价值、主题倾向和叙事风格都比较吻合。小说的魅力在于文字之间的想象力和虚构的场面性,而电影的魅力在于它的再现功能和独特的影像叙事能力。五代的代表人物陈凯歌和张艺谋都在各自的电影创作中,很好的将他们的影像表现手段与影片的精神价值和叙事做了尝试性的结合,也得到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而他们对于情节剧,亦或是悲剧,亦或是戏剧张力较强的影像叙事能力,也在《霸王别姬》和《活着》做出了极佳的展现。诚然,近些年他们的影片质量难能说是上乘,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归咎于“顺势”而流,被浮躁和没有指向的中国电影创作环境所搅扰。
个人觉得,仪式感在张陈的电影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往往也是深刻揭示整部影片主题的一个利器。《黄土地》的“求雨”、《红高粱》的“高粱地媾合”都是突出的典范,应该说这种仪式感是整个西北地区独特的人文历史和生活环境所导致的,它必然深深刻在了西北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中。电影《白鹿原》也有仪式感,在预告片中的“草垛子做爱”便有了这样的意味,但是实际在影片中,这样的画面清一色的消失掉了,连最重要的“求雨”都消失无踪。《白鹿原》上映之前打出的口号就是“渭河平原的史诗”,史诗电影在中国并不多见,仅有的具有中国烙印的史诗电影中,都带有极为深刻的“仪式”烙印,《霸王别姬》中有,《活着》也有。称之为“仪式”不如说是“隐喻”更为贴切。这种表现在大场面、小场面的“仪式”感,其实就是导演本身主观阐释主题的一种“隐喻”。从戏剧性的角度说,电影《白鹿原》中白嘉轩剪辫子其实可以做成一种“隐喻性”,“念乡约”自然也可以弄成一种隐喻性,但是实际上都被导演模糊的主题倾诉,莫名其妙的影像风格阉割完毕,成了既不是驴,也不是妈的骡子了。
四、断裂的叙事线
电影《白鹿原》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导演根本没有讲清楚故事了。
电影中主要的人物角色有以下几个:
白嘉轩、鹿子霖、黑娃、田小娥、白孝文、鹿兆鹏、鹿三。
仔细看几遍电影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导演讲清楚了。电影叙事最主要的就是叙述一件完整的事件,这个事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来龙去脉”。剧作法中的“来龙去脉”来自于美国著名的剧作家西德菲尔德的《电影剧本写作基础》,我们前面定性了《白鹿原》最好,也是最应该改编的方向是将它改成一个情节剧,那么这个“来龙去脉”必然适合。即便不按照这个套路走,一部电影中最起码的将人物要干嘛,为什么做讲清楚也是必然。实际上在电影《白鹿原》中呢?可能出了田小娥的线索是相对比较清晰之外,其他人都是断裂的。而田小娥,恰恰是原著作者在上述几个人中着笔最少的。即使她再重要,也不该在这样一个以宏大叙事为前提下的史诗叙事风格电影中占据第一要位。当然,导演完全可以以田小娥作为核心专门拍一部旨在表达“女性的悲剧”的《田小娥传》。
白嘉轩是原著的第一主角,他身上担负着整个渭河平原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他是忠实于这块土地的,他就是代表,“人与土地命运的抗争”也主要是通过他来表现的。同样,“两代人的价值取向”也少不了他的参与。而事实上,这个如此重要的人物在电影中,起到了“催租”、“封建家长”的作用,他身上所承载的那些关于“土地”、“命运”和顽固不化的思想都没有清晰表现。其他人物也都是这般。导演处理人物显得过于仓促和单薄,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表象,而没有深入灵魂深处的拷问和对答。很多时候,这些人物都是说变就变了,前面出场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再次出场就已经脱胎换骨,中间很少给出线索让观众自发的去连接和遐想,几乎变成了导演要你看他们的命运,而不是观众判断他们的命运。
纠结这点其实有些过分,毕竟是删减掉了一半导致的叙事线索断裂。但是我依然要摆清一个观点,删减掉一半的不是观众,而是导演本身。
电影《白鹿原》很清晰的将中国当前电影创作的一些悲苦状况赤裸裸的呈现在了大众面前。为了商业而创作出来的永远不可能是艺术,它必然是一种泡沫式的幻想。而在《白鹿原》身上所清晰表现出来的导演的急功近利,并由此而导致的叙事混乱,同样也是一种写照,亦或是一种警示。导演王全安的自以为是,是导致电影《白鹿原》失败的表性因素,而大量商业侵扰、名利诱因必然也是罪魁祸首。从芦苇的剧本中看,电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有精神指向,也有完善的外表,而从电影《白鹿原》看,这只是一个被爹娘生错了的畸形儿,被化了妆放在大众面前讨要掌声的小丑作秀而已。电影的根本是什么?在这部电影的成败背后给出了一个答案。电影的根本,首先是一个故事,其次,这个故事有着清晰的主题,有着对民族文化的解读,有着完整的结构和影像技术,还要有更多的坦诚和诚意。
路漫漫其修远兮!